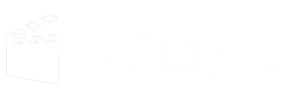令尤庆感到惊异的是,他的卧室地板下藏了一个尸体。
尸体的颜色是黑色的,记得打开地板的时候,一股乌烟升起,遮蔽了尤庆的眼睛。尤庆看着黑色垃圾袋里透出的模糊肉块。善良的他安慰自己道:“这是猪的尸体。”可是,等他遮住鼻子小心的打开塑料袋,他看到了一个人的脸——无比空洞又无比灰暗的一张脸,它的眼睛早已呆滞。鼻子粘合在脸上,像是随时都会掉下来。尤庆把火烛伸近了它,诡异的事情——那张脸是个笑脸。
那天晚上,尤庆并没有睡很好。他躺在自己房间里的那张竹床上,尸体的恶臭被门外的凉风裹挟着飘向他脸的上方,他正在出神地望着头顶的天花板,思考着尸体的笑脸。
死去的人是有毛病么?要是没有的话,他怎么会笑着死呢?一个疑问顶在尤庆的头顶。不过,一个更大的疑问从他的脖子爬上头颅,一拳把先前的疑问打倒,成为他现在心头最大的迷惑---尸体在地板上摆着,他该怎么处理它呢?
他想起了一件事,这间屋子的主人其实不是他,而是一个满脸胡子的吝啬鬼。记得还是一个午后,吝啬鬼在浇花,尤庆则站在他身边,和他谈着住房子的事。
“房子可有些年头了,一时让给你,我还舍不得呢。”吝啬鬼的水壶对着尤庆那张恳请的脸。水壶这头,是吝啬鬼那张有着诡异的脸——和尸体一样的笑。
尤庆像明白了什么,怪不得吝啬鬼急着把房子让出去呢。老头子还真是狡猾,按尸体的腐烂程度,应该是在尤庆搬进来前后死的。要是尤庆叫警察的话,警察怕是会怀疑他。
那么,尤庆该怎么办呢?他从床上起身,时间还早。尤庆走到窗台,见到了对面房屋里漆黑的一片。尤庆有主意了,他把尸体再次装好在塑料袋里。小心地开门,吱呀一声,外面的月光照进屋子来。外面很静,风吹动树叶的幽语音。门外出现一个人斜拉着的臃肿的影子,当然,是尤庆了。他把塑料袋放进裤腰袋里,虽然现在外面基本上没什么人,但是尤庆得做完全的准备啊!尽管有些别扭,尤庆还是逼着自己接纳了冰凉的塑料袋。尸体的肉块柔柔地在尤庆的裤腰带碰撞着他裸露的大腿,不时传向大脑一阵阵的刺激。
到了对面的楼房前,住在里面的是吝啬鬼。尤庆曾向他借一条鱼,但是吝啬鬼不借给他,还骂了他一通穷光蛋之类的话。尤庆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,呵口冷气。月亮正在头顶,该动手了。
吝啬鬼和他的老婆睡得正香,尤庆小心靠近门。推推,推不开。尤庆只得从门边出来,在吝啬鬼家的房前转圈。发现了他……
您没有登录,注册并登录后方可阅读全部公开的正文!
免费注册 | 马上登录
尸体的颜色是黑色的,记得打开地板的时候,一股乌烟升起,遮蔽了尤庆的眼睛。尤庆看着黑色垃圾袋里透出的模糊肉块。善良的他安慰自己道:“这是猪的尸体。”可是,等他遮住鼻子小心的打开塑料袋,他看到了一个人的脸——无比空洞又无比灰暗的一张脸,它的眼睛早已呆滞。鼻子粘合在脸上,像是随时都会掉下来。尤庆把火烛伸近了它,诡异的事情——那张脸是个笑脸。
那天晚上,尤庆并没有睡很好。他躺在自己房间里的那张竹床上,尸体的恶臭被门外的凉风裹挟着飘向他脸的上方,他正在出神地望着头顶的天花板,思考着尸体的笑脸。
死去的人是有毛病么?要是没有的话,他怎么会笑着死呢?一个疑问顶在尤庆的头顶。不过,一个更大的疑问从他的脖子爬上头颅,一拳把先前的疑问打倒,成为他现在心头最大的迷惑---尸体在地板上摆着,他该怎么处理它呢?
他想起了一件事,这间屋子的主人其实不是他,而是一个满脸胡子的吝啬鬼。记得还是一个午后,吝啬鬼在浇花,尤庆则站在他身边,和他谈着住房子的事。
“房子可有些年头了,一时让给你,我还舍不得呢。”吝啬鬼的水壶对着尤庆那张恳请的脸。水壶这头,是吝啬鬼那张有着诡异的脸——和尸体一样的笑。
尤庆像明白了什么,怪不得吝啬鬼急着把房子让出去呢。老头子还真是狡猾,按尸体的腐烂程度,应该是在尤庆搬进来前后死的。要是尤庆叫警察的话,警察怕是会怀疑他。
那么,尤庆该怎么办呢?他从床上起身,时间还早。尤庆走到窗台,见到了对面房屋里漆黑的一片。尤庆有主意了,他把尸体再次装好在塑料袋里。小心地开门,吱呀一声,外面的月光照进屋子来。外面很静,风吹动树叶的幽语音。门外出现一个人斜拉着的臃肿的影子,当然,是尤庆了。他把塑料袋放进裤腰袋里,虽然现在外面基本上没什么人,但是尤庆得做完全的准备啊!尽管有些别扭,尤庆还是逼着自己接纳了冰凉的塑料袋。尸体的肉块柔柔地在尤庆的裤腰带碰撞着他裸露的大腿,不时传向大脑一阵阵的刺激。
到了对面的楼房前,住在里面的是吝啬鬼。尤庆曾向他借一条鱼,但是吝啬鬼不借给他,还骂了他一通穷光蛋之类的话。尤庆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,呵口冷气。月亮正在头顶,该动手了。
吝啬鬼和他的老婆睡得正香,尤庆小心靠近门。推推,推不开。尤庆只得从门边出来,在吝啬鬼家的房前转圈。发现了他……
您没有登录,注册并登录后方可阅读全部公开的正文!
免费注册 | 马上登录
编辑:青梅煮烈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