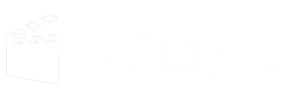山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;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自从赵宋南渡,杭州便成了京师——临安,临时安全,一时间,这临安府歌舞升平空前繁荣。
南渡的人里,除了赵宋宗室、官僚集团、士农工商之外,更有许多辽金西夏蒙古的细作卧底,其中就有一个金国细作,买了身份证毕业证,一番拼搏,知识改变命运,居然做到了临安府的宣慰使,自称是主人翁。
主人翁大人育有一子,名衙内翁,虽然也是说汉话着汉服,但骨头里还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苍茫与无羁,若在大漠草原,必能成为矫健勇武的部落统领,然而生在江南长在江南,一出家门就是人挤人人挨人,又寻不见了林教头的娘子;闭门不出,自己的爹娘又总是神神秘秘,不搭理自己,背着自己不知道捣鼓什么。孤独啊,百年孤独,每日只好呼朋引类宴乐骑射,驱车狂飙,只是不该把这临安府里的里弄街巷视作荒滩戈壁,把街上的行人摊贩视作草芥砾石。
这主人翁卧底多年,建功甚多,现又位高权重,金国狼主为了奖赏笼络,便把一架汗血宝车赏赐给了主人翁。偷运到家之后,因嫌此车在街上太过招摇,自己还要作廉洁的大宋宣慰使,便存而不用束之车房。岂料,一日衙内翁宴乐歌舞之后,正意兴高涨百无聊赖,一眼瞅见,上去一试,呵,这动力,这流线,这音响,此车只应天上有,临安能得几回见。走,上车,出去让土包子们开开眼。同伴们瞅了瞅日头,道:现在正是放学下班时间,街面上人太多,别花了咱的车,不如等宵禁以后,再跑个痛快,如何?衙内翁不悦道:信不过我?怕死就滚。众人只好附和,蜂拥上车,呼啸而出。
一路的夸父追日风驰电掣,见缝就钻,哪里人多往哪去,过街穿巷,越店掠铺,大脑的热度随着发动机的转速越来越高,直逼极限。同伴眼尖叫道“慢点!前面安全岛上有人。”“狂飙为我从天落!”衙内翁像烈士就义一般,狂呼口号,快车加油一脚到底,狂飙过处,只见一片黄叶迎风而落。
却说那梁山好汉武松,自折了一臂,又眼见山寨众人落得如此光景,烦恼心起,封金挂印,挎了戒刀,走到这人间天堂,爱惜这里的湖光山色疏影横斜,便在六和塔下,结庐而居,参禅习武,悟道修行。
一日正在打坐,忽闻远处有人啼哭,哀婉凄惨,令人垂怜,想这周遭素来人迹罕至,何人会来此啼哭?武行者开了柴扉,循声望去,只见在歪脖树下,有对老叟老妪正在相拥而泣,来至近前细一端详,两位老人像是远道而来,风尘仆仆形容枯槁,正哭得……
您没有登录,注册并登录后方可阅读全部公开的正文!
免费注册 | 马上登录
自从赵宋南渡,杭州便成了京师——临安,临时安全,一时间,这临安府歌舞升平空前繁荣。
南渡的人里,除了赵宋宗室、官僚集团、士农工商之外,更有许多辽金西夏蒙古的细作卧底,其中就有一个金国细作,买了身份证毕业证,一番拼搏,知识改变命运,居然做到了临安府的宣慰使,自称是主人翁。
主人翁大人育有一子,名衙内翁,虽然也是说汉话着汉服,但骨头里还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苍茫与无羁,若在大漠草原,必能成为矫健勇武的部落统领,然而生在江南长在江南,一出家门就是人挤人人挨人,又寻不见了林教头的娘子;闭门不出,自己的爹娘又总是神神秘秘,不搭理自己,背着自己不知道捣鼓什么。孤独啊,百年孤独,每日只好呼朋引类宴乐骑射,驱车狂飙,只是不该把这临安府里的里弄街巷视作荒滩戈壁,把街上的行人摊贩视作草芥砾石。
这主人翁卧底多年,建功甚多,现又位高权重,金国狼主为了奖赏笼络,便把一架汗血宝车赏赐给了主人翁。偷运到家之后,因嫌此车在街上太过招摇,自己还要作廉洁的大宋宣慰使,便存而不用束之车房。岂料,一日衙内翁宴乐歌舞之后,正意兴高涨百无聊赖,一眼瞅见,上去一试,呵,这动力,这流线,这音响,此车只应天上有,临安能得几回见。走,上车,出去让土包子们开开眼。同伴们瞅了瞅日头,道:现在正是放学下班时间,街面上人太多,别花了咱的车,不如等宵禁以后,再跑个痛快,如何?衙内翁不悦道:信不过我?怕死就滚。众人只好附和,蜂拥上车,呼啸而出。
一路的夸父追日风驰电掣,见缝就钻,哪里人多往哪去,过街穿巷,越店掠铺,大脑的热度随着发动机的转速越来越高,直逼极限。同伴眼尖叫道“慢点!前面安全岛上有人。”“狂飙为我从天落!”衙内翁像烈士就义一般,狂呼口号,快车加油一脚到底,狂飙过处,只见一片黄叶迎风而落。
却说那梁山好汉武松,自折了一臂,又眼见山寨众人落得如此光景,烦恼心起,封金挂印,挎了戒刀,走到这人间天堂,爱惜这里的湖光山色疏影横斜,便在六和塔下,结庐而居,参禅习武,悟道修行。
一日正在打坐,忽闻远处有人啼哭,哀婉凄惨,令人垂怜,想这周遭素来人迹罕至,何人会来此啼哭?武行者开了柴扉,循声望去,只见在歪脖树下,有对老叟老妪正在相拥而泣,来至近前细一端详,两位老人像是远道而来,风尘仆仆形容枯槁,正哭得……
您没有登录,注册并登录后方可阅读全部公开的正文!
免费注册 | 马上登录
编辑:看江湖